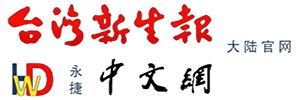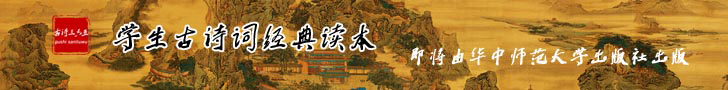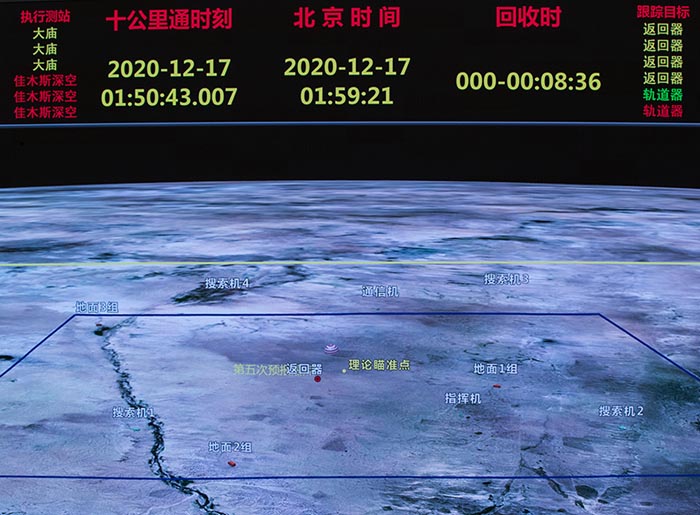人說敦煌的鳴沙山月牙泉,一生中總要來一次。而在今年8月初訪敦煌之後,回到台灣,我的耳朵就經常不自主的持續耳鳴,有點像是夜晚的鳴沙山,狂風吹來,沙子稀稀疏疏作響。彷彿回音不絕於耳,不時對我召喚,然而小弟也是凡人一介,並非草木,豈能無感?一如我對敦煌,始終揮之不去的思慕,和日以繼夜的懷想。

小弟今年已然奔六,在我們那個年代,唸國中時,喜歡給同學取綽號,可能因為我常當班長,所以分得到的綽號,還不太離譜,叫做〈隴阪〉。現在的人聽來一頭霧水,完全無法想像。原來這個專有名詞,出自於當年的國中地理課本,讀到甘肅省這一章的時候,甘肅簡稱甘或者是隴,而隴阪的意思,指的是甘肅省東邊有隴山,它的關隘或是山坡就叫做隴阪。而且隴字通壟,意思就是田埂,引申為陡峭的山坡之義。例如唐代詩人盧照鄰,有一首〈入秦川界〉的詩,第一句就說〈隴阪長無極〉,可以為以上的說法做見證。

但問題是,甘肅省的這個地理景觀隴阪,跟我有什麼關係?原來是當年青春期荷爾蒙格外強烈,臉上的青春痘如雨後春筍,各自盛開爆裂,尤其是我的前額這一大塊沃土,本來應該渾圓平滑的額頭,現在因擠壓青春痘而凹凸不平,看來一如甘肅省,崎嶇不平的隴阪地形,所以小弟當年的俊俏英姿,無以名之,就被同學用隴阪來形容,當時一如災難現場的尊容,當年小臉受災的慘況就可想而知了...

而後上了高中,就和文前標題提到的三毛有了關聯。高一當校刊副主編,不才自詡是文藝青年,而另一位副主編,是日前才謝世的知名作家,此處只是磨蹭名人的光環,但也藉此說明當時社會的文化氛圍。高中時讀了三毛的〈撒哈拉沙漠〉,也興起了朝聖三毛的想法,有次她在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,下了課我跟志同道合的同學,趕了好幾班公車前往,一走下公車就呆了,現場人山人海,排隊等待進入演講廳的群眾,繞了國父紀念館一大圈,有點像是繞樹三匝。後來當然是進不去,無功而返。於是我們在現場發飆,對我們後面一大堆也向隅的群眾說,聽不到三毛沒關係,我們這一邊有一毛半來演講,請大家捧場。最後當然是沒有人理我們,被當作是神經病發作,穿的還是高中生卡箕制服呢...

今年8月初訪鳴沙山,沒想到10月而已,受到北京謙哥和春雨馮博士的邀請,我又回到敦煌。然而三毛何在呢?原來三毛在生前曾經說過,希望一半葬在台灣,一半就放在鳴沙山上,甚至她把地點方位都選好了。多麼空靈玄妙的作家三毛,千挑萬選找到了鳴沙山作為他的歸骨所,這座山我來過兩次了,根本就是神山。簡單說就是黃沙蕩蕩,純然潔淨的沙粒堆起山丘,白天艷陽高照,遊人如織,已經是驚艷絕景。但是夜晚大西北的狂風,又將山丘吹聚得更為高大挺拔,流沙伴隨風聲嗚咽,四面八方作響,據說是五音齊鳴,一如仙樂飄飄。山腳下還有月牙泉幽靜清新,但是它玄的是,既找不到地底源頭,也不見其它入水口,但是千百萬年以來,滋潤西北大漠眾生,狂風吹不去,太陽曬不乾,問君哪得清如許?可能源頭活水就在你我的心中。

而當年的高中生,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與三毛緣慳一面,小弟今天二訪鳴沙山,還是沒看到三毛的落腳地。當然全世界三毛的文友,可能早就想在她選定的方位處,修個衣冠塚,或立個紀念碑之類。但是回想三毛一生作品的言行和性格,如果此處成為觀光勝地,旅遊景點,不是驚擾嗎?與其張揚喧嘩,不如低調安靜,於是焚化遺物,化作灰燼,融入鳴沙山的塵土沙粒,也許更適合三毛的純真性情,歸於塵土,讓真摯的魂靈安住於此。

三毛最後的著作〈滾滾紅塵〉,既有書本,也有歌曲,還有電影,流傳於世,讓她的讀者可以時常懷念。而她的魂靈,回歸分屬台灣的日月潭和敦煌的月牙泉,如此一來,天上的月娘啊,只要是月光所及之處,都有一個三毛,永遠住在你我的內心深處。